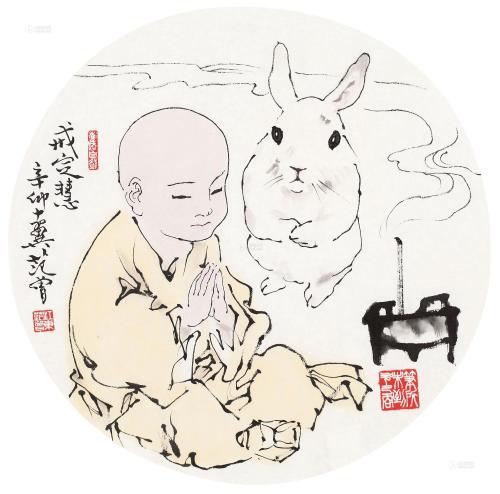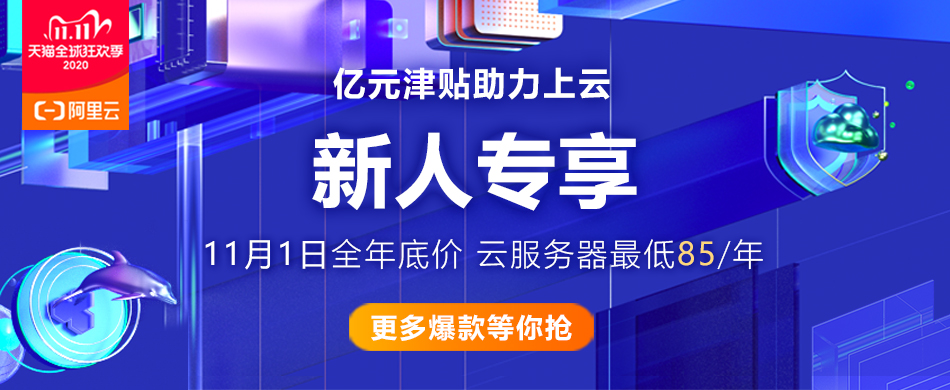新冠肺炎期间,这些诗火了!网友:这也算作家?
向来热衷于说人话、做实事,不过自从疫情以来我看到的这些妖魔鬼怪实在太多了,总想着跳出来骂他们几句,否则如鲠在喉实在难受。
每逢灾难,就总有些***跳出来“歌颂”,我也不懂他们是有病还是脑残。
2020年疫情以来喷娃看到的第一篇“马屁仙人”,当属写出“我要感谢你,冠状君”一诗新冠诗人。
这首诗简直和“我要感谢那些给予我痛苦的人”如出一辙,搞得好像白衣天使要像他证什么,老百姓要向他证明自己多善良一样,真特么奇怪。
接下来就是黄冈市一位“才子”写的诗,当然这也是一首“夸人”的诗,把上级夸的是“眼里的血丝,已织成了迎春的花卉”看得我“石碾流泪,林风儿销魂”。
当初我以为这已经是“顶配”了,直到昨天发现,还是小看了这群货的风骨,简直可怕!
散文学会会员于中华老师他来了,他带着他的诗走来了——《万岁!心中的太阳!》。截一小段大家品品!
看!你打电话“控制疫情源头”,而拥有数千万人口的“武汉”在一夜之间关闭了这座城市!
有多少优秀的中国孩子。
看!你打了一个电话
努力成为抗击流行病的志愿者!
它越危险,就越向前。
它越危险,就越有攻击性!
……
请相信我们的聚会
大海充满了自然的色彩。
100年考验越来越清晰。
你曾经害怕过风雨的起伏吗?
你竟敢带头扭转局势!
真特么是舔到灵魂深处,醉倒云里雾里,第一次见有人能把诗写的这般清新脱俗,也是一种本事了。
究竟得多弱智的人,才能把一场灾难描绘的如此动人,你丫语文老师是不是没教你别把白的说成黑的,别把丧失当喜事办?关键这特丫的需要别人教吗?
这三人不愧是接连着出现,真尼玛一山还比一山高,你们算是让我见识到了什么人人外有人了。
于中华老师不愧是曾任这些职位的人,我记得他还出了本书叫《当官是一门技术活》,他又一次诠释了这本书名的意思。
疫情期间这群写“赞美”诗的脑残,他们有一个拿手绝活,也可以说是吃饭本领,那就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不用怀疑,就是面对一坨屎,他们都能称赞三天三夜。
现在都是如此了,也不知道疫情结束后,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来!
大家还记得当年地震王兆山得名“王幸福”的神作吗?“看奥运,同欢呼。纵做鬼,也幸福。”
还有不甘其后的“余含泪”!
现在第三人隆重登场了,他就是写《万岁!心中的太阳》的“于太阳”!
多地也不骂了,祝舔的愉快!
国家不幸诗家幸:那些跪舔的马屁“诗人”
读到了一篇文章《出现了!最无耻的马屁诗人出现了!》,文章列举了几个马屁诗人借着这次疫情跪舔的事例:
《我要感谢你,冠状君》是这样写的:
黄冈市某县政法委的一位干部是这样写的:
还有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于中华写的《万岁!心中的太阳!》。这种作品令人作呕!只能算是会写简化字的匠人,说他是诗人,都是对“诗人”这个词的侮辱。
……
我们统称这类人为“马屁精”。
“马屁精”是个大群体,又可以细分若干个小群体,这几篇“诗作”的作者因擅长写诗,就可被称呼为“马屁诗人”。
因为千穿万穿马屁不穿,也因为某些领导喜欢有人“吹捧”,因此,在疫情得到控制后的一段时间内,这些“马屁诗人”(当然还有马屁作家等)会越来越多,越来越有市场。
我看到2月2日《文汇报》对这类现象的评论:
“面对灾难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,越应该有高规格的要求,越应该有高质量的保障。而失去对生命的敬畏、对价值的尊重,类似‘感谢,冠状病毒’这类‘作品’,只是借着文艺的名头乱作为,既无法减轻疼痛愈合伤口,更不能留住记忆提供反思。”
(纠正一下《文汇报》:感谢,冠状病毒,是题目,应该用书名号而不是引号,即《感谢,冠状病毒》)
这个评论中规中矩,不是我想要的。
我想要的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评论,或者说渴望一种辛辣的讽刺。
直到我看到清代文学家赵翼《题元遗山集》中的两句诗:
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始工。
这个味儿就对了。
回顾历史再看看现状,可不就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嘛。
越是乱世,社会秩序越是动荡,就越是出诗,出诗人。
当然,这些诗有些是千古传诵的经典,诗人也是中国文学璀璨的明珠,如身处安史之乱的杜甫与他传世的《三吏三别》;
当然也有很多滥竽充数、沽名钓誉的马屁诗人,如前面列举的那三位。
这样看来,如果抛去道德评论,马屁诗人与他的作品算得上是“应时之作”。
马屁诗人不仅是“应时”,因其“极端敏感”,善揣摩人心理尤其是知道领导的“痒点”在哪,故也懂得“应势”。
应时+应势,虽不能保证千古留名,但短期内还是能够名利双收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看,那些批评马屁诗人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“无病呻吟”,就有点“too young too simple”了。
(收藏本网站,请持续关注浏览本网更多信息,获取更多内幕消息!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