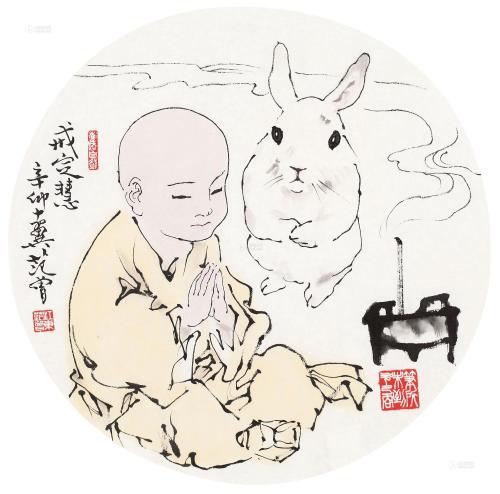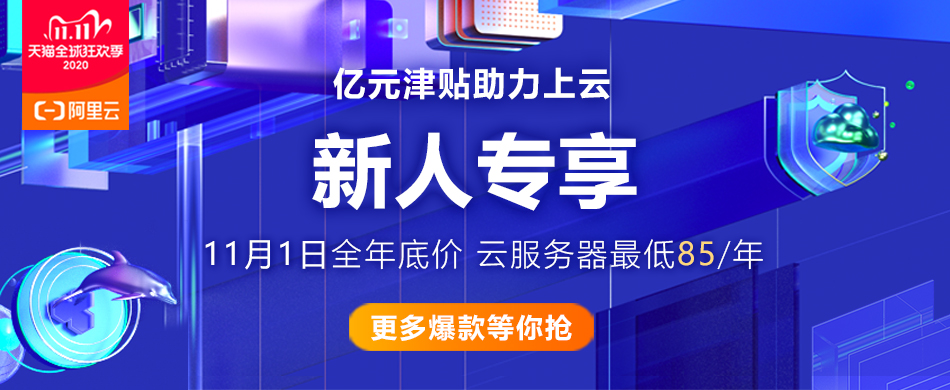边写边发,方便阅读,请添加关注
【精简前言】本人土生土长的农民,艰苦的经历锻造了坚强的性格与做事原则,永远不会丢掉淳朴、本真。
《甘肃老家,70后的窑洞生活》描写我本人的亲身历程,力求真实呈现我们那个年代的沧桑岁月。
通过撰写本文,寄希望于现在的青年人、学生能珍惜当下,励志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!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《甘肃老家,70后的窑洞生活》
我家坐落在黄土山坡上,因王家户大,故名王家边边。近临是张家壕壕与刘家梁梁,组成沿用至今的中滩社。
1983年,姐姐17,已嫁人两年。哥哥15,已辍学四年。妹妹9岁,没上过一天学。我12,在离家对面约二里路的中滩小学上四年级。父亲在去附近山上找羊,滑倒滚下悬崖,二十多天后村民发现尸体,仅剩三分之二。母亲,从此孤身艰难的抚养开始……
(接上连载)
“喔喔喔”,“六五,上学了,鸡叫了!”母亲在暗地里急促的叫道。
听到叫声,我看了看哨眼(窑洞上沿打一个斜洞,通向外面用来换气、见光,如下图),微弱的光线,能感觉又是明亮的夜空。翻了翻身,揉揉眼,一骨碌灵光的从炕上爬起来。哥哥、妹妹还在酣睡中,没有看出一丝的警觉!
天麻亮了,背上书包,听到我家小花汪、汪几声,传来远处的跑步声夹杂着喊叫,是张家壕壕的学生过来了,不约而同的每天一起出发。通常情况下,我出发,母亲也出发。我和同学一起上学,母亲和毛驴一起耕作。
中午需要回家吃饭,不带回书包,方便去校时背上拾粪的背篼,下午放学收获点牛驴粪便,供烧火做饭。每天中午回家,母亲定是做好了饭菜。农闲季节,一家人会一起填肚子。遇到农忙,哥哥妹妹也下地里。我回家,厨窑是上着锁的,抬开门,钻进窑洞打点肚子。
一天两餐。午饭散饭,晚饭面粉变着花样,时而疙瘩汤,时而白水切面,时而酸汤长面。
用的清油,省点用,一瓶(500ml)擦锅煮菜可用半年。
大户农家都有养猪,残汤剩汁洗碗水,加上野草伺候,吊打上一两年,过年前一两个月再贴点米糠、麸子,很快,猪长了肥膘,人也长了精神。
过年前谁家杀猪,热闹劲赶上现在的姑娘出嫁,大户会请上党家邻居一二十人吃杂碎。有时我家也杀猪,上窑炕上坐的尽是分量重的长辈,厨窑大多是女人和孩子扎堆。没有赶时来的,在队里有些资历的老者,母亲会派我们把饭菜送到人家里去。杀猪算是大事,互请大家补点油水,已约定成俗。
猪油炼了,加上盐搅和,装一坛子,两三年够了。
我家,地处干旱地带,雨雪极少,靠天吃饭。尽管每户土地都不少,我家就有近70亩,但每年多半养,少半种。不养不行的,否则连种子都收不回。我家多数都种五谷杂粮,有小麦、谷子、糜子、扁豆、荞麦、胡麻等。一年下来能收一石多点,缴完公粮所剩无几。一旦遇上三、五年大汗,公社会拨点救济粮。多为苞米、红薯片。
吃的水,遇上大过雨,窖里能引进些泥水,运气好了能装满一窖,沉淀沉淀,算是解决了大问题。水得省着用,洗脸时,常常一碗水一家人轮着,母亲习惯垫后。洗完脸的水倒到桶里,以备家禽家畜饮用。
村里的人们,都习惯了盼雨!偶尔看见头顶黑云,人们会聚集场头(场头就是农村合作社时用来集中堆放麦垛的地方),一起眼巴巴的求雨,十有八九都是一阵风刮走了期盼!
在我的记忆中,吃水,三分之二时间都是在下游约四里路的腰环湾。那里上天恩赐,打出了一口地下水井。平时捞坝有存水,我们村里使用不要钱的。队里的牲口都是在那里饮水,走时驴用桶驼,人用担挑,连吃带拿!
务农,是重体力活,耕、磨、种、锄、拔、收、碾。我家劳力全靠母亲、哥哥,收成永不及他人,所以常吃救济粮。一到冬天,经常是熬肠刮肚、杯水粒粟。趁我寒假之时,便与母亲出去讨饭,到有山偏雨光景好的村庄讨些米面,已解断粮之困。